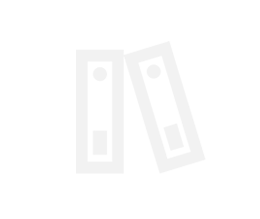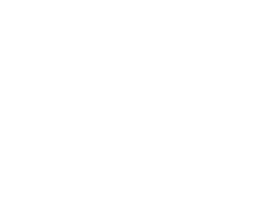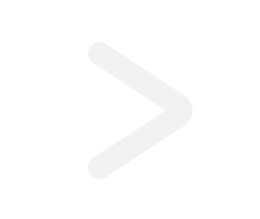抗生素耐药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全球危机。
美国应对治理问题设立特别小组今年4月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至少有70万人死于耐药性疾病,其中23万人死于耐多药结核病。如果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最糟糕的结果是全球每年可能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性疾病。
自青霉素发明以来,人类和细菌的战役永不停歇。上一代的抗生素出现耐药性,下一代抗生素顶上来,甚至可以说,滥用抗生素所带来的耐药性在不断督促人们生产新的抗生素,以应对随之而来的新问题。
前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施贺德博士曾表示,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全球将走向后抗生素时代,普通的感冒也能置人于死地。
按常理来说,抗生素被滥用导致了公共问题,研发抗生素的药企,应该如研发肿瘤药物的药企一样,每当有新药上市,它都可能是市场上的一颗新星。如果幸运,他们可能像PD-1一样,面对着肿瘤这类公共卫生问题带来的庞大市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还能顺手成为一代药王。
但是,事情却远非如此,药企却担心这个烫手的芋头。
稍有留心医药行业新闻就会发现,最近有关抗生素的新闻是成功研发对抗耐药性超级细菌的抗生素公司Achaogen破产了。全球医药巨头,诺华、阿斯利康、赛诺菲也都放弃了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的研究。
此前GSK抗生素研发部门主管佩恩曾表示:“现有商业模式的投资回报与所付出的努力并不相称。”
但是当你扫过国内的抗生素使用市场,就会对此心存疑虑。
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主任郑志杰分享了一组数据:“我们每年生产了16万吨的抗生素,一半是人用,一半是兽用,中国是第一大生产国,而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也是第一大消费国。”
上面是整体抗生素市场的情况,人用药物市场的情况是2017重点城市公立医院TOP50药物中,抗感染药物占据首位,用药金额达89.08亿元。而这只是一部分医院的数据,在抗生素滥用问题最为严重的基层市场上,这个数字还不算什么。虽然“限抗令”来了,但看起来抗感染药物的市场仍然坚挺,在庞大的市场面前,为何药企纷纷跑路?
从种类来看,在2017年国内使用的抗感染药物中排在前列的有恩替卡韦、美罗培南、伏立康唑等。以美罗培南为例,培南类抗生素问世时间为上世纪80年代;再看同样排在前列,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头孢类抗生素,第一个头孢菌素是上世纪60年代上市的,临床上多在青霉素耐药的情况下使用;而青霉素类作为最早的抗生素,问世时间还要再往前一点,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菌,治愈了梅毒和淋病。
这就是问题所在,目前常用的抗生素上市时间较长,新的抗生素被发明乃至上市时,并不会立即使用,市场的反馈和研发投入远不成正比。英国的一项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7年获批的16种抗生素中,只有5种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形容新的抗生素像是一把被束之高阁的钥匙,在已有抗生素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它不会轻易的被使用。
“针对耐药性疾病,即便开发出新药,也往往必须等到有耐药性的病原体爆发才能将新药投入市场,高昂的研发成本和较低的经济效益导致许多药厂缺少动力投入。”对药企而言,在抗生素药物研发中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和投入,无法直接变现,“这是没有商业激励的,所以一些药厂不断缩减这方面的投入,或者裁撤整个部门。”
在各种耐药菌中,耐药结核似乎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的全球结核病报告中,提到结核病主要发生在生活贫困的人群、边缘化的社区和群体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中。而正是由于此,结核病也被称为“穷人的疾病”。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结核耐药情况愈发严重,中国是耐药结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相较于普通结核耐药结核,耐药结核患者负担更重,大约需要20万-30万元。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估计,2017年全球范围内应该有1000万结核患者,结核病发病率为133/10万。但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结核病的发病率早已低于10/10万人。
和抗生素问题不同的是,结核病、耐药结核在发展中国家是拥有广阔市场的,但是对于药企来说,这群支付能力不强的患者似乎还不足以支持他们研发新药。“不是妖魔化药企,药企毕竟是营利企业,没有商业利益,药企也没有办法继续投入研发到其他药物。”丁胜博士说。
“激励药厂去研发抗生素,大家都讨论过很多次了,世界经济论坛、博鳌论坛,各个国家卫生部门都在呼吁,也有政府主导的激励措施,比如说针对同一家企业的其他药品优先审批等,但还是不能阻止药企(退出抗生素研发),大家一直在探讨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去解决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大药企不看重发展中国家结核病这种不赚钱的病种,他们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肿瘤、糖尿病市场。我也在想,是不是由于药企不愿意研发,在抗生素和抗结核药物这种经济效益不高或者贫困人群的疾病上,才需要政府、慈善不求经济效益的投入?比如像Gates Foundation这种不求回报给钱到一些公司、大学,这个过程是不是必须由政府或者慈善基金来主导?”界面新闻在采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首席运营官陆漫春博士时,问题又被抛了回来。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还无解,也并未有哪一种模式被证明行之有效,只不过政府和慈善基金的介入,能让企业不那么窘迫。《商业周刊》曾经报道,那家研发了新型抗生素倒掉的公司Achaogen,曾从政府机构和慈善团体中获得2.5亿美元的捐赠用于研发。英国的生物医药研发慈善基金会Wellcome Trust此前曾经出资支持印度一家制药公司,进行耐多药结核药物的研发。
在国内,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也在探索一种可被复制的中国模式,来解决新药研发带来的挑战。GHDDI选择结核病、疟疾、寄生虫感染这类研发经济回报较低,但是对公共卫生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疾病进行药物研发。
“药厂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还必须有人去做。我们想,能不能由像我们这样的非营利的机构来主导研发,政府和基金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当疾病爆发的时候,我们有药可用。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机制,我们也希望这个模式成功后,能被复制。”丁胜博士说。
高兴的是,GHDDI最近已经和Scripps Research合作发现了能有效治疗丝虫病感染的抗沃尔巴克氏菌全新化合物,或能成为治疗丝虫病感染的临床候选药物。GHDDI的模式仍然在探索。
悲观的是,研发新药会越来越难,药物并不是无穷尽的,在化药、生物药研发井喷后,我们已经离那个天花板越来越近了。而在这种情况下,研发的速度想要追上耐药的速度,也会越来越难。
抗生素不是无穷尽的,更何况,抗生素研发还这么惨。